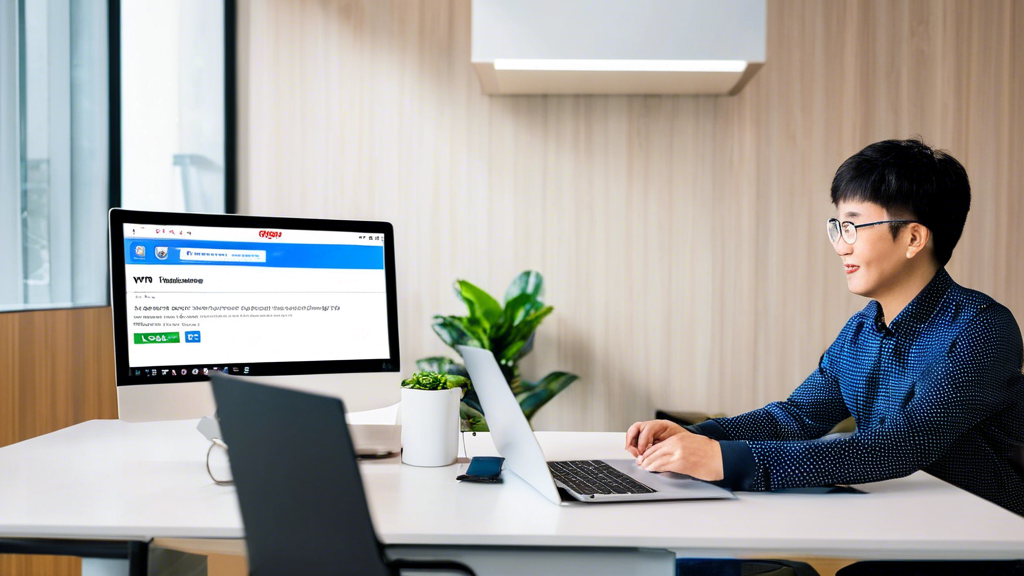「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
改编自小说《魁儡花》的公视大河剧《斯卡罗》堂堂完结,从首播到落幕,这部戏的收视越飙越高,引起的争议话题也越来越多。有人赞赏它还原史实,重现那个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也有人不认同它过度改编,美化部分角色之余还参杂了当下政治氛围;还有人对最终结局感到错愕不解,逼得导演曹瑞原不得不亲上火线,在个人脸书连发两篇短文释疑……撇开纷议、单论制作品质,耗费钜资、动员广大人力物力的《斯卡罗》,的确是近年台剧中的杰作。先送上大结局精华剪辑。
《斯卡罗》大结局精华版
早在开拍前,曹导就透露过:「即便是一个被所有人当成大坑的案子,他都想完成一个叙述台湾第一次浮上世界版图的时代故事。」被《斯卡罗》当成主轴的「罗妹号事件」,统治势力不下於清廷的琅峤十八社,以及牵涉其中的李仙得、必麒麟、卓杞笃、潘文杰、刘明灯……这些一度左右了台湾当年命运的历史人物,到了现代,如果不是钻研史学的专家学者,究竟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人事物?陈耀昌医师的小说《魁儡花》,当然在书写技巧和铺排结构上有其未尽之处,当中对史料的取舍及还原度也多有存疑;但是从文学价值的角度看,试图去重写一段即将被後世遗忘的历史,本身仍是一件有意义的行动。如果我们把《魁儡花》视为基於史实的二创文学,暂时忽略其中有意无意的加添改作,那麽曹导将其影视化的《斯卡罗》,因应剧情需要进行重新梳理、美化、还有新增的人物及改写,自然也都有其存在必要。
「当太阳闭上眼睛时」
根据曹导在脸书的释疑,他在改编《一把青》时采用了平视视角,把观众放在与剧中角色同样高度的位置,让观众在随着角色的感受去进入那个时代。但在《斯卡罗》,他把观众提高到了接近全知的俯瞰视角,因为剧中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如果只让观众定睛在某几个人身上,就很容易被角色框架限制而看不清全局;但给观众一个了解宿命因由的全知视角,却是理解故事脉络的必要条件,所以他在剪接上做了与以往相当不同的改变。换言之,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与原作小说不同的故事,也与我们往常看到的曹导作品有很大的差异。
而对於某些人基於各自的历史认知或意识形态,给这部戏强加的政治正确(或不正确),曹导的解释是:他只想让戏剧回归到人性。也就是说,蝶妹也好、李仙得也好、乃至於必麒麟、潘文杰都好,这些角色在剧中呈现的迷惘、追寻、和身分认同,是在那个时代洪流下注定的宿命;现代观众对角色群的认同与不认同,其实也不过就是对自身身分认同的二度投射。曹导也说:我们对这块土地应该更有信心,但也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建立自信。
「你从海的背面来」
尽管曹导努力释疑,但《斯卡罗》全剧出现的问题,也不仅止於剧情上给各有身分认同疑惑的族群带来的不同代入。纯粹以技术面看,曹导重建场景、还原时代的能力相当优异,画面取景的空间美学也优於其他商业剧导演,但除开这些,《斯卡罗》在视听感受上还是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配乐音效,二是演出表现。
先说配乐音效,《斯卡罗》的插曲及配乐是由陈小霞和张艺共同打造。两人先前已经和曹导合作过《一把青》,这次分别担任音乐总监和配乐编曲,每首歌曲无论曲调的抓耳程度、曲风的时代氛围、配器的编排协调,都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但是落实到剪辑搭配上,却总是让观众觉得过度饱满、甚至喧宾夺主。主因还是後制时没有计算留白比例,整部戏没有适度的给予观众静心聆听台词的空间,而且衬乐进出点往往十分突兀,没跟上剧情当下所需要铺陈的情绪。当然观众们不可能都是音乐专业,不会在乐理上挑剔,但视觉与听觉终究是连动感官,一旦其中之一察觉违和,另一也多少会受到影响,从而降低入戏程度。
演出表现的部分,问题比配乐来得更严重。曹导擅长以镜头、画面叙事,但从他所有作品看,他并不是位很能要求演员感受力的导演。在他的戏中,一旦出现多位演员同框的场面,往往就会呈现各演各的状态,形成一种「不在同一个时空」中的扞格;演员本身的演绎能力越好,和其他角色间的互动违和就会更强烈,让情感的互动变成了情绪的互斥,这种现象在《一把青》当中就经常发生。出身自不同领域、养成环境相左的演员,本来一定有各自擅长的演绎手法,有人会缩在角色後面、有人会穿上角色外衣、还有人会把突出於角色,导演在现场必须说戏教戏,让演员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但我们在曹导作品中常见到的,却是把现场主导权全部交给演员,以至於在《一把青》已经出现过的问题,到了《斯卡罗》尤其强烈,明明有众多优秀的演员齐聚一堂,交织出的成果却往往是互相抵触拖累。
以上就是以个人观点,对《斯卡罗》一剧落幕後的一些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