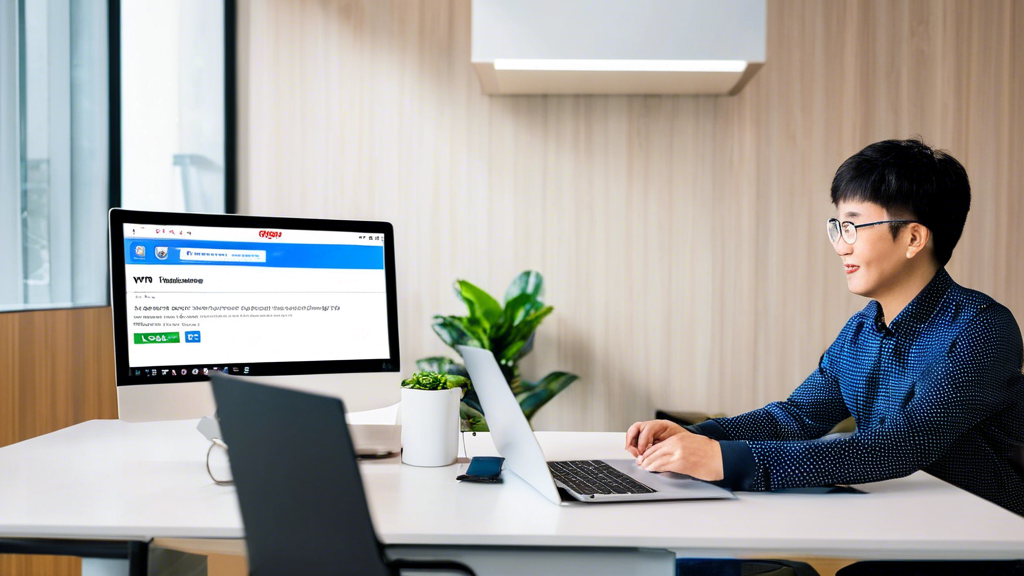这出戏架空在一个叫作「平霖市」的都市,像是拥有蝙蝠侠的万恶城市,不是芝加哥或是纽约,而是充满犯罪的「高谭市」。架空城市场景的设定,让这个台湾剧组拍摄出来的故事不再被局限在台湾影视作品有许多都是台北或高雄发生一─它可以是台湾任何一个都市,甚至可以当作所有以中文而主语言的都市。换句话说,这个英文片名为「The Victims’ Game」的故事,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开启这个游戏。
这平霖市透过镜头,不曾放晴,阴暗,像是有一股浓的化不开的纠结,布满在这个虚构城市。宛若这出戏里,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却得不到的快乐,想忘却忘不掉的痛苦。过气歌手的痛苦,渴望性别认同的痛苦,职场、家庭、前科,就连这出戏里要让观众跟着他们一起推理的角色──赵承宽的家庭里拥有疏离,方毅任的亚斯伯格症让他陷入家庭悲剧,看似什麽都不在乎的记者徐海茵,也被锁在小时候父亲自杀时充满废气的汽车里,始终都没离开过。
每个人的痛苦,都有各自的故事及细节,但这世上,人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又有谁会花费心力去听一个不知道他的痛苦是真是假的故事,但这其实就是这出戏的主题──要怎麽去听他人的故事。
在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的报导文学《地下铁事件》里,村上春树在最後一章「没有指标的恶梦」写着:
「人们多半已经疲於再接受复杂的、『既是那样,同时又是这样』的复合性、多重性——而且包含背叛的——故事了。正因为己经无法在那种表现多重化之中找到自己置身的场所了,因此人们才要主动地把自我丢出去。」
在《谁是被害者》里的所有被害人,拥有各自痛苦的他们,在社会里失去了自己的立足之处,透过让自己去完成下一个被害者的遗愿,像是将自己的人生丢出去,从戏里的角度来看,在我们以为是在追查现在这位死者的过去,其实这是下一个死者的人生,而当观众已经知道了下一个死者「为什麽他要自杀」的同时,他却硬生生地在故事里死亡,而又开启了下一个死者的故事,不断地丢出及进入的过程里,这是《谁是被害者》这出戏的这场游戏里,描写细节的方式。
一个人身上有着各种细节,这些细节构成一个人的存在,构成一个群体生活,而当所有细节聚集成概括到数百万数千万人的群体、我们会称之为「社会」的世界观里,这太庞大而且太繁复了,每个人都只能去在乎自己想看的细节,越简单越直白越好,而其他的事情都变得微不足道似的,这样的冷漠一如徐海茵在报社的上司,把所有的细节都看作是一场有利益可赚的生意。而当我们无法从他人的细节找到共呜,失去了同理心的时候,这个社会需要的是像《谁是被害者》这样的连续剧。
以八集为架构的《谁是被害者》,虽然在制作上比较取向欧美剧的方式,但我觉得这出连续戏比较偏向日本 WOWOW 台擅长的剧种──约四到五集就完结的悬疑推理剧。制作上精良,在一定的篇幅里有条理地说完背景、案件及推理,塑造出凶手的「恶」的过程,以及最後希望观众相信「善」的结局。我通常不会觉得这样的一出戏,是能撼动产业的惊人之作,或是它给予观众另一种全新的解读观点,但它往往会显出这个产业模式下的细水长流,确实且完整地说出整出戏想让观众得到的讯息。
透过 Netflix 的播映,剧组在每集的最终都会放上制作花絮及导演编剧访谈,在第七集的花絮里,《谁是被害者》的编剧之一徐瑞良说出了我觉得他们在《谁是被害者》里确实做到的事情,也是全戏核心:
「它比较像是一个永远不会停下来的辩证,也许我们可以放弃去找所谓它有一个正确答案,或一个正确价值观的这个想法。不要停止去探索这个问题。」
我想,剧组将天地无限的原着书名的「第四名被害者」,改为这个问句剧名《谁是被害者》的用意,是因为他们清楚这出戏提出了许多深重的社会问题,但我们都很清楚这些问题,并不是一出戏剧能够改变或是能确实给观众真相,但它的好,在於问题呈在观众面前後,让现在的我们去思考怎麽倾听他人的故事,同理他人的细节,努力不让这问句里的「被害者」,出现在我们实际生活的每一个都市里。